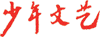|
|
最遥远的距离(2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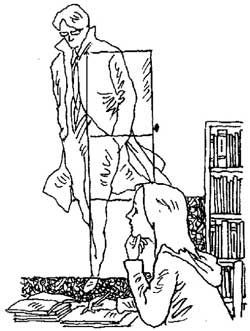
2
我从来只佩服一个人,那就是妈妈,我学得和她一样爱嘲弄人,爱惹别人伤心———她用小说我用言语。我小时就对着镜子练就了她一样的不屑的微笑,以及她思考时把手放在额头的姿势———但我仍旧不是她,我没有她那样敏感的下巴,滋润的嘴唇,孤傲的鼻梁和柔软的身段,所以她永远是光彩照人,我仅仅只能是惹人注目;她的锐利吸引别人,我的锐利逼走别人;她左右逢源,我独来独往。我其实妒嫉妈妈,非常非常。
可是你有一双灵动的眼睛,有一天林扬这样对我说,他是第一个发现我的美的男人,也是第一个我爱上的男人,第二个我佩服的人。
林扬就住在学校宿舍里,冬天的傍晚,从阅览室的窗子里可看见他低着头在小树林里散步,双手插在大大的风衣口袋里,耳朵藏在高高竖起的衣领下,脸上全是晃动的树影,有几次他就擦着阅览室的窗走过,离我那么近,我可以清晰地闻到他风衣上阴冷的味道,晶片状的小颗粒缀到了他的身上,亮闪闪的,他的人从窗口走过,而他的影子总是拖得很长很长,很黑很黑,慢慢悠悠地好久才移过窗子。
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,林扬的身子又会变成一阵风,穿行于教室外的走廊,黑色的休闲西服显出他修长的身材,我必须跑着步才能踩上他身后的影子,抱着书本追到办公室,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一下子长大,成为他的伴侣,这样挽着他的手臂就不会害怕跟不上他;我常常又希望自己突然变得很小很小,可以撒娇,成天粘在他身上,这样就不会害怕被他甩到很远。
“我的课代表又要问什么题呢?”他漫不经心地叼住一支烟,回头冲我扬起眉毛,然后就低头,看我的题和一旁密密麻麻的解答,我知道他从没有一次把我的解答全部看完,就突然抬眼望着我,吐出一大团烟,眯起眼:“你知道让我做我会怎样办?”他不是要真的等我回答的,他紧接着就拿起手边的笔,写得那样随意却又胸有成竹,仿佛仅仅是在写自己的名字一样,有一缕头发总会落到他的前额,在纸上投出一个奇形怪状的影子,像是他的解答一样让我着迷———简单直接,却让人意想不到。他是一个高超的玩家,饶有兴致地玩着类似那种环环相扣的锁链游戏,许多人怎么使劲都解不开,林扬却总是知道这些题目的玄机,轻易就破解它们。他写完就立即把笔扔得远远的,起身面朝窗口,用那烟雾缭绕的后背对着我,不再理我———我带着羞涩享用这整个过程,就像那年背着父母用精致的高脚酒杯品尝绿薄荷酒———正是那种冷酷又高贵的液体在吸引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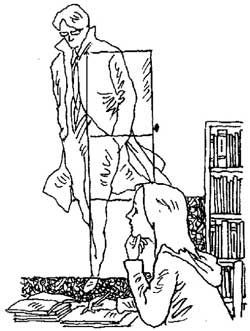
有一天我与林扬偶遇,我蓄谋已久的偶遇啊,在黄昏的小树林里,捧着一本《泰戈尔诗集》,专注地看啊看啊,步子慢 慢往前踱啊踱啊,就被林扬挡住去路了。我就死死低着头看书,生怕一抬头眼眶里含不住的快乐就要喷涌出来。一大片忧郁的黑影如移到头顶的乌云,蒙到了书页上,烟草的味道又冷又阴沉,林扬的身子俯得很低,好奇地捕捉我躲藏的目光:我的课代表要问题目吗?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?我咬着嘴唇,说得有点艰难。
什么?这是哲学吗?
他直起身子,但是没有转过身去。我仍低着头,偷偷瞥见他皱着眉,然后遭遇到了他的目光,隐约闪烁着,是不安是期待,或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,也许是那书中的咒语正悄悄飘逸出来,使我不由自主地翻到了他写着一首诗的那一页,送到他手上。
骤然地,我从没见过他眼里有这般的光亮,灼痛了我,是燃着的火,他从回忆里复苏了,火映红了他的额头和脸庞。爱抚着情人的脸庞一样,他爱抚着泛黄的书页,纤细的手指仿佛是被柔情的液体浸润,他就像个迷失的孩子,不断地摇头,他的喉咙深处发出叹息,支离破碎的,是痛苦的呻吟,他拍拍我的肩,如梦中呓语:丫头,回去睡觉吧。我哽咽了,身体有一处在作痛,一会比一会剧烈,是这里,就在左边的肋骨稍稍偏上的地方。
学校的小树林到了黄昏会有不同的颜色,有时是玫瑰色的,有时是棕黄的还带着点烟尘,有时是蓝紫色的有点潮湿。太阳是个钟摆,摇落了天边的云霞,天就黑了。我把这些发现都告诉林扬,我们早已经常在一起散步了———偶遇的次数多了就会变成心底的约定———林扬说,你有一双灵动的眼睛,他的烟头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地冒着火光,鼻梁如黝黑的山脊。我说,是吗是吗,那是遗传了我妈妈的,可惜其他地方都不像妈妈。
一双灵动的眼睛就够了,那时我就是迷上了一双眼睛,夜晚的时候,就像有无数的星辰揉碎到那双眼睛里,斑斓璀璨,我忍不住就要去吻这双眼睛。
林扬不说了,投向我叹息般的一瞥。
告诉我,后来呢?她离开了你?她伤了你?林扬只是摇头,把烟熄灭,丫头,该回寝室睡觉了。
寝室,多么令我讨厌的地方,因为寝室楼里的所有女生都讨厌我。很奇怪,女孩们在某些时候会突然间变得很团结,互相都成了好姐妹,是的,她们团结起来讨厌我,独行的林扬身后竟然跟着个踩着他影子的女孩———既不美丽高挑,也不温柔贤淑———太可恨,简直不可容忍,亵渎了她们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偶像。最让她们生气的是,我甚至一点都不怕她们,还那么挑衅地在她们面前晃———我是故意的,故意把林扬给我的全国数学竞赛参赛证压在玻璃台板下,故意问他要来平时用的钢笔写作业。
女孩们背地里叫我刺猬,刺猬!———妙极了,我喜欢这个绰号。林扬也有个刺猬的绰号,恨他的同事们就这么叫他。真是很少见的那么多不同的人如此团结对付一个刺猬,是啊是啊,凭什么不安分教现成的书却自成体系,什么“林氏定理”,什么“林扬黄金定理”,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怪方法,一步就猜对答案,最最可恶的是他总是一针见血提出老方法的漏洞,他教的理科班总是抱回最多的奖,好吧好吧,没有你林扬不行,但你就这样了,不会再怎么样了。
林扬问我,为什么我们两只刺猬不会互相刺痛呢?他哪里知道我的刺在他面前就蜕化了,只有他刺我的份,但我没办法了,我决定牺牲自己的刺,是写那句诗的女孩说的,两只刺猬不可能在一起,那我就不做刺猬了,我也许会被刺痛,流出血来,甚至痛死,而他会不会懂得帮我止血?我的刺长不出来了,我目睹着自己越来越苍白,越来越瘦瘪,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,他还会不会说我有一双灵动的眼睛?我不管了,我中邪了,毅然决然。
你近来吃炸药了?挺能上火啊!母亲的表情很奇怪,居高临下的,似乎有先知先觉的功能,怜悯地像看一个傻瓜一样看我———让我痛苦至极。我原来真的以为她会欣赏林扬,我怀着怎样的渴望让她分享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一切,但我们说着说着———说着林扬———我的声音就要突然提高,兴奋变成愤怒,每次都是如此,我受不了她总用不以为然的眼神冷冷看着我,嘴角升起的嘲笑更是令我怒不可遏:“无可置疑,林扬是个天才!”
“他只是个最最普通的小教师罢了。”
“不,从任何细微处就可见———至今,其他平庸的数学教师只知道笛卡尔右手坐标系,从没想过像林扬用左手,腾出右手写字。”
“那他干吗不用脚趾?!”
“他会的,如果他的脚趾能弯成那样,他会腾出左手吸烟———他吸烟的姿势多优雅多高贵,手指纤长,夹着烟,他是个诗人,数学王国的诗人,特级教师们只不过是搬运工———把书本上的东西死死搬到黑板上,而林扬才懂公式的和谐,数学的美……”我知道我在嘶喊,我要拼命拼命地捍卫———捍卫我自己,捍卫我第一次的爱情。
“可他从来都是个失败者,爱情的失败者,事业的失败者!即使是诗人也是悲情诗人,落魄诗人!你这个傻姑娘,收起你不切实际的幻想,他和我同岁,他的年龄可以做你爸爸了!”
空间静寂了好久,蓄积的怒火和勇气被压回胸腔,结成一块冰,心胀得很痛,像被炸裂开来,碎片在体内到处飞扬,然后是耳鸣,嗡隆嗡隆,是妈妈的一字一句,一遍紧跟一遍,重重叠叠,重重叠叠。
我多么不愿承认,但林扬确实老了,那被潜意识隐去的细节清晰地重现,我多么不愿承认,但那正是衰老的迹象:他低头时,我见到他的发路,周围的发根都是灰白;他夹烟的左手背上,有两个褐色的斑点;他的额头,弯弯曲曲地横着两根皱纹,在他抬眼看我时就变得很深。我是多么多么不想承认这一切!
声明:本文由著作权人授权新浪网独家发表,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。
网友评论
相关链接
- 黑星 2005-07-14 10:16
- 每一个小孩都会犯错 2005-06-22 10:20
- 用什么丰富孩子精神世界 2005-06-03 09:07
-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2005-04-11 10:39
- 不测是人生的一个险滩 2005-04-08 10:24